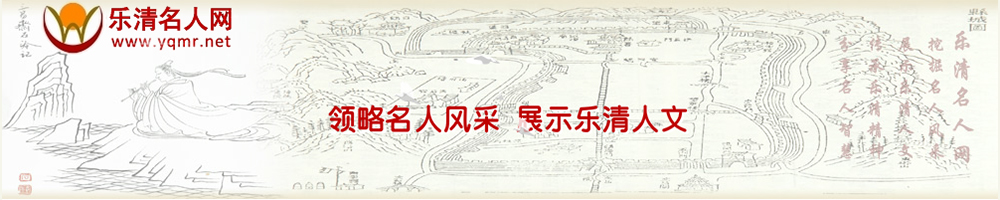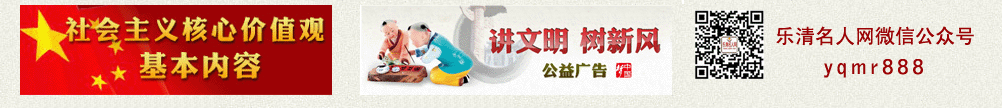,因为东君对少年时是否习过武这事总是三缄其口。
东君所在的乐清柳市,是一个大集镇却是一个小地方。电器、公司、股份集团、企业连锁、塞车、忙乱、金钱,这种八仙桌上生猛盛宴式的风格是这个地方的特色。东君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写作。由于东君在这么一个地方生存,就有很多人曾经担心东君的生活来源与生存问题,说,一个作家怎么能在这么一个地方生活写作呢?这些人的想当然的担心应该是有些道理的,对一个书呆子式的写作者,这种担心是成立的。但是,东君的生存能力并没问题,因为东君是柳市上池村人,柳市是温州最发达的城镇,柳市上池村人能够不去赚钱养活自己么?一个各方面能力都不错的人要是在柳市解决不了生存问题,要是生活得太寒碜,那还是柳市人么?如果是那样一个连自己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柳市人,当你走在柳市街上,或走在上池村的巷子里,不被柳市人骂死才怪。所以,他们对东君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东君也曾在一家县报当记者,对东君而言,当记者有什么好,难道比在柳市生存更好么?东君最后辞掉了记者职业回柳市自办了一个工作室,这个新职业对东君远比在报社自由也自在了许多。东君还在县报的时候,会常到文联的办公室里来聊天,同来的常常还有吴玄或简人。吴玄常把脚跷到办公桌上侃大山,把烟抽得云天雾罩,天南海北地神聊,东君自然也参与其中,但东君的话没有他们俩多,谈文学的时候,东君常常都保留自己的看法。我那时看他,想,东君年轻,是一个对文学有野心的青年。那时,东君与吕不还一起办了一个民刊,叫《蠹》(当时曾有人把“蠹”字误读为“蠢”)。东君叫我也拿了篇随笔与一首诗放到里面。那刊物的封面一边白一边黑,就一个刊名“蠹”字在上面,封面设计出自东君之手,显出与青年不相称的一种老成与深沉。这刊物好象只办了一期,不知是经费还是其它问题,再没有第二期出来。在报社那段时间里,他写出了第一部中篇小说《人·狗·猫》,写出来后很快就发在了《大家》杂志上。《人·狗·猫》,是一种自由的书写,杂糅了随笔、辞典、笔记等文体。我以为他的这种文体是对当时在报社受约束的新闻文体的一种反向写作,他是为内心的自由找到了一个释放方式。我想,相对于当时的生活现实而言,那时的东君是不是有意要在小说中实现一种内心与书写的自由?
回柳市之后,东君一是认真办起了一个排版工作室,那些年,柳市多如牛毛的民营企业正蒸蒸日上,拼命装出很有企业文化的样子,几乎每个稍大点的企业都有一份企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