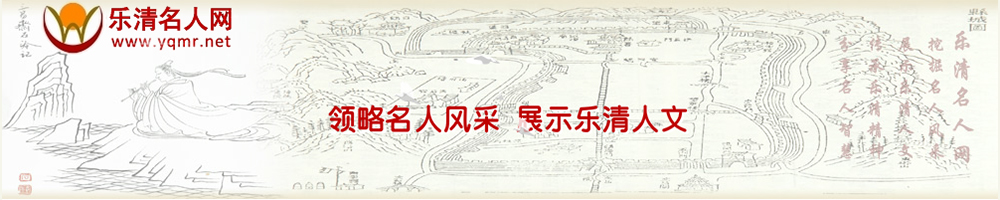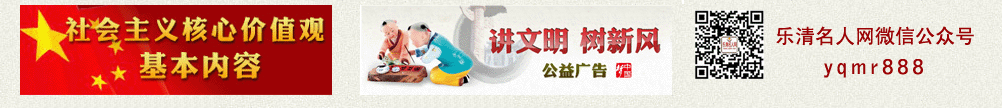。
乐清日报:这篇短篇小说看似简单其实挺复杂,单就故事来说,除了洪素手弹琴之外,其间还穿插着她师兄徐三白的小故事,还有她师傅顾樵兄弟的小故事,唐书记和唐老板父子的小故事。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策略是不是与古印度的《五卷书》及后来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东君:这我倒是没有想到。之前我的长篇小说《树巢》是有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叙事策略。在这篇小说中,我下功夫较深的是语言。我们这里的一些方言是很有意思的,譬如“佛”,有月光佛、石头佛,甚至还有鼻涕佛。鼻涕佛是什么意思呢?以前在乡下若有小孩常常流鼻涕,大家就叫他鼻涕佛。后来我想想,其实这“佛”是持久、久远的意思。还有温州人常见的“阿渠”,我在《听洪素手弹琴》也用到,在温州方言中这是个人称代词,但不确定指向谁,如果只有你在场,那就指向你,我认为这是温州方言中的“第四人称”。我的大部分小说都会挑选这样的一些方言词汇,我觉得这些方言词汇能激发我的思维。我的写作从广义上说还是普通话写作,但并不是纯粹的普通话写作,我们是南方人,如果纯粹用普通话写作,思维就会被北方的语言带走。看鲁迅的文章,他也是很谨慎地使用北方的语言。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小说有南方特色,我觉得就是语言上和他们用的不同。《听洪素手弹琴》投到《人民文学》时,当时的主编李敬泽说:“你的故事发生地点在北京,怎么没有北京的语言味儿?”我说:“这是南方人在北京,他们在语言上还是坚持南方的习惯。”在这篇小说中,顾樵的侄子平时说北方话,但和他叔叔顾樵说话时就用南方话。从这些细节处,我们可以体味到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不会轻易被同化的。
乐清日报:唐书记和唐老板一个是官,一个是商,唐书记听琴是把它当作医疗保健用品,唐老板听琴是把它当玩偶,他们从表面上看是在“养活”艺术,其实是在摧毁艺术。正像当今社会有人把艺术家当成门下的清客,有人把艺术当作牟利的“股票”一样。《听洪素手弹琴》表达的东西看似幽远神秘,其实内在的意蕴却相当尖锐,我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诠释过度?
东君: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很多东西都被市场化了,但是有很多东西要拒绝融化。现在的社会,很多的东西都被同化掉,能够坚持的已经很少了。在这篇小说中,洪素手只是一个符号,她可以是一个琴人,也可以是一个作家、书法家,也可以是诗人、画家,在这个时代他们要坚持一些东西已经很困难了。琴者情也,这篇小说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