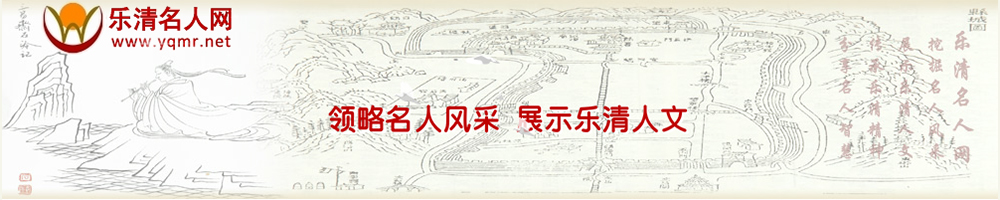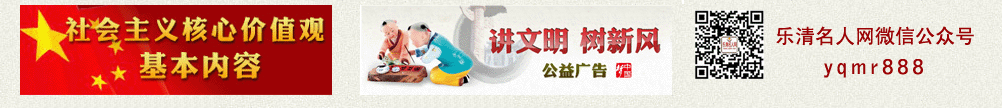具有浓厚的中国画气息。
昌谷同志的用色之所以使人感到鲜艳,正是由于他善于运用冷暖色的对比,这种对比色彩的变化,使画面产生新鲜感,这种从传统中来的手法,在昌谷同志的作品中,却是新的、发展了传统的中国画。
在笔墨方面,昌谷同志爽健的用笔和淋漓痛快的用墨,是经过艰苦的基本功锻炼出来的。中国画强调“有骨有肉”,也就是既见水晕,又见线条。昌谷同志是善于笔墨结合的。他认为山水画中“干裂秋风,润含春雨”,“润含春雨”的滋润效果是主要的,“干裂秋风”是衬托对比的手段。在本画册中,我们可以品味他的这种见解的实践效果,从而发现他在笔墨方面的功力。
书法和绘画,两者不但是“同源”,而且是互相为用的。昌谷同志的书法,我觉得是从潘天寿、以至八大山人的风格,受到影响,流鬯质实两者结合得很好,同时和他的写意画风,更十分和谐。他的画法功力,已到了从心所欲地达到他自己的笔墨效果,具备自己的面目。晚年的行草,更接近八大。周昌谷在八大的基础上,更加以发展变化。八大的书画都不易学,昌谷有此造诣,是很难得的。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画,始终趋向于革新,如果以黄宾虹、潘天寿为第一代,那么像周昌谷这样的第二代,从题材到笔墨,也都具有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内涵。真正懂得中国画的人,总觉得中国画还有挖掘不尽的潜力。当然,形势要求我们的中国画更进一步地反映时代,革新是永远不会中止的。否则,中国画就不能百花齐放,就缺乏生命力。
我和周昌谷同志第一次认识,记得是1957年春,在山西永乐宫邂逅的。他到永乐宫临摹元代壁画,我到那边是搜集一些中国美术史资料。但分手不久,一浪接一浪的风波,知识分子们都主动地“相忘于江湖”。现在回忆,1957年昌谷正是二十八岁的峥嵘岁月,我那时则是四十四岁的壮年。光阴飞速流逝,现在我已八十四岁,而昌谷离开我们,已经十一个年头了。
作为同时代人,我有幸比昌谷寿命长了些,既然一生爱好美术,觉得更有责任把我们时代的一些俊杰之士,以及我们这时代的艺术风貌,向今人及后人推介。因想,青年时代就创作《两个羊羔》从而为我国获得第一次国际金奖的昌谷同志,如果在他以后的艺术生涯中,少受些别风谁雨,他的寿命与成就,当不限于这本画册的辉煌。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国家民族都处在新形势下,深愿今后的画家能在无忧无虑中,进行繁荣的创作。
注:“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系苏轼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