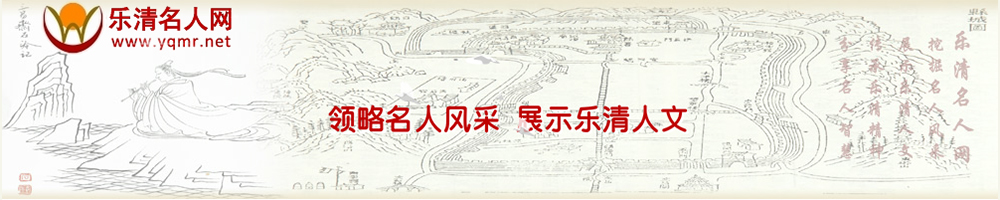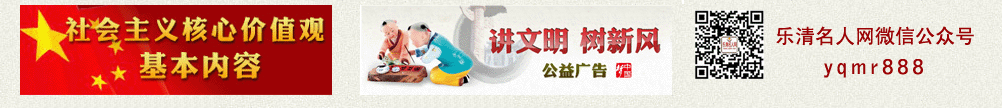在这时(1950年12月)被选调到华东空军第六预科总队的。半年后,经过考查筛选,选调进入长春东北空军第一预科总队。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徐柏龄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除白天8小时坚持上课外,晚上还加班加点刻苦自学文化,提高文化素质。
1952年7月,徐柏龄跨入哈尔滨空军第一航空学校,这里是进入空军飞行员训练的第三关。从这一天起,他才算是正式的飞行学员。经过多次筛选,到这时随徐柏龄一起从陆军转来的100多人,已所剩无几。
两年多的航校生活,徐柏龄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三种机型的飞行训练。
1954年11月,徐柏龄从航校毕业,这时朝鲜战争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战斗也告结束。此时中国民航要发展,缺少飞行员,于是,徐柏龄被分配到民航工作。起初,徐柏龄认为民航是地方建制,希望自己能到部队去,有机会参战,能当英雄。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因此,1954年12月,徐柏龄与30多位同学一起踏上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来到了中国民航局。
当时正赶上中国民航与中苏民航公司合并。飞行队伍中既有国民党两航起义(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的飞行员,又有苏联的飞行员。徐柏龄被分配到由苏联飞行教员带飞、执行北京至苏联边境伊尔库茨克的国际航线,开始驾驶的飞机是“苏式立二”。
在空军航校徐柏龄是学习轰炸机的,现在改飞运输机,任务和性质完全改变了,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困难接踵而至。徐柏龄所在的机组由4人组成,三位是苏联人,机长(教员)伊凡诺斯金,报务员、机械员也都是苏联人,唯独徐柏龄这个副驾驶员是中国人。机上没有乘务员,是由报务员兼管客舱服务工作的。徐柏龄没有学过俄语,连字母都不认识,困难可想而知。每次北京起飞之前,先由翻译在机下帮助苏联教员给徐柏龄讲解飞机课目。飞行过程中他们语言不通,全靠打手势理解教员动作。
语言不通,学习飞行困难,同时给生活也带来许多不便。起初徐柏龄根本吃不惯苏联西餐,蒙古——乌兰巴托机场餐厅的牛羊肉味道使他更难受,一进餐厅,他就“饱”了。于是徐柏龄每次出差只得带几个苹果充饥。
为了沟通联系,徐柏龄每次飞行都带一个小本子记俄语单词,向苏联教员学习俄语。他强背硬记,慢慢就学会了一些。后来,他不仅跟苏联教员沟通了学习和生活用语,而且还可以在飞行中与伊尔库茨克塔台指挥员建立通话联系。徐柏龄深有体会地说:“生活是逼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