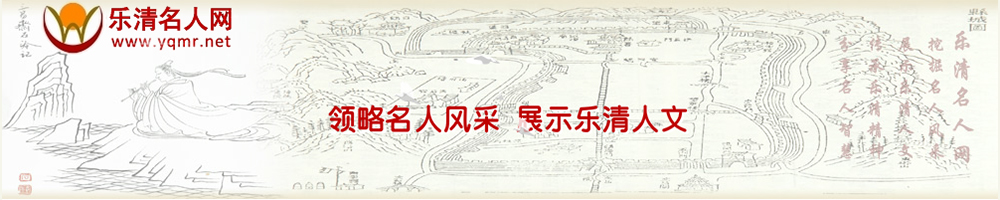讲台擦毕,收拾来苏布回袋开始上课。“我啊,我这辈子与艺术分离不开了”这是开场白,我们听了半年。后来还教我们书法。说是上书法课,其实都没怎么教,就叫多写。无论看谁的字必来一句:蛮好蛮好,好兮。
其实书法课更像国文课,教授如何欣赏古典文学。先生教法是唱读的,一篇“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唱读下来,已是半节课了。接着在黑板上画幅图,解释诗文意思。每次讲解完毕,强调几句:国画是用线来表达的,就那么条线,要表达一些内容,所以格调要高,要读很多书。国画一定要接近文学,才有意境。我也写了那么多年的书法了,感到字比画还要难,画不好了,可以浓的再来一笔,字写不好了,就不好了,马虎不得,要下真工夫。啊,啊。我讲的不一定对,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啊,啊,退班(下课)。
王老上课从不带讲稿,皆即兴发挥,但由于牙齿缘故,发音有时不太准。也因有时咿咿呀呀地吟唱,后来有些同学听不惯,不愿听王老的课了。一年下来听课的学生,只剩十几位了,后来这十几位同学成了王老晚年关系最亲密的学生。用别人的话讲,就是关门弟子。
二
真正接触恩师,是1996年夏天。
学校暑期开国画培训班。起先报名的人很多,大概是食宿自理的原因,后来上课的人只有我一个(先生是免费授课)。10年后,同学们都开玩笑:我们的门生身份,是站在门口的学生,你门生身份,是坐在门槛上的学生。
先生家住在北门,学校在乐湖路口,每天必来,一起作画,写字,作诗,谈乐清风物。来时先检查前一天的习作,再讲解技法。然后各自画画。那年,我开始了小说的写作。写了个长篇《年轻人的回忆录》,文中的男主角何雨多愁善感,其实也就是以自己为原型写的。那年学校的情况也复杂,再加上家境不好,面临很多选择问题,文章结尾有段话:冰冷的风夹着蚕丝般的细雨,慢慢织成一张无限惆怅的网,在黑夜的那边,徐徐向我扑来。今夜,只有阶前一株小草陪我坐着,我甚至听见了草叶上划落的水滴那一记重重的破碎声。我就是飘着的雨,流着地上,淌向何方?
先生看了文字后,很是开心地和我说:“画家就应该会写文章,会作诗。坚持下去,就会一步一步接近成功,妙悟艺术真谛。”现在想来,那篇文字粗劣幼稚得很,可是先生非常婉转指出:“一定要多写,多想,多读书。还有,你的笔名糊涂逸人不好,逸人就逸人,也可以。糊涂什么?青年人,看山就是山,糊涂不得。现在有些迷茫,是正常的,我也迷茫过。每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