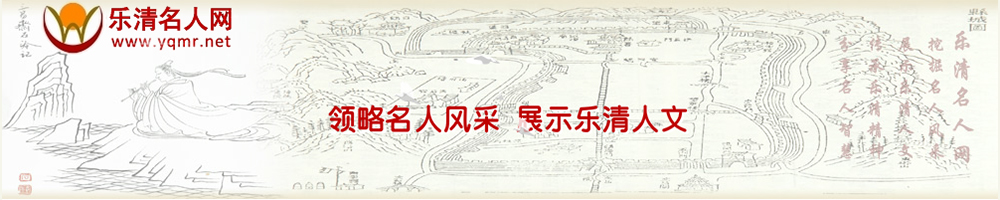书桃源”题额,还为我画了插图,并赐大作《再忆黑白版画大师—张怀江先生的从艺艰苦伟大的历程》,而且多次打电话关心杂志出版情况。但是由于我懒惰及其他原因,至今未付梓。未能在先生有生之年赠阅,真的很惭愧很内疚。
先生独爱榴花,斋号榴花书屋。先生爱雨,斋名“云语楼”、“觉云斋”。而先生走的时候,正是榴花盛开,雨声淅沥。如此巧合,莫非冥冥中之天意否?王老走好,一路走好。
记思雨先生(节选) ■尚洪浦/文
1995年初秋,我就读于东方艺术艺校。那时我穷,学校也穷。我着了件表哥穿剩下送的衬衫,参加学校在某医疗器械公司借来的会场举行的第一届开学典礼。如没记错,主席台上坐着的是林子津、朱一正、许宗斌、王桂南、王思雨诸先生。入坐后,一位头发卷得与方便面一样的老头,从包里拿出一条白色尼龙袋,抠出一块灰黑色的布,随手抓来一瓶矿泉水,很认真地擦起瓶盖,依序擦了瓶身,瓶底儿。随后站起,递给坐在身边的许宗斌先生:喝水,喝水。许先生起身推却:不渴,不渴,不用,不用。王老师硬塞:拿住拿住,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喝瓶冷水,已经实在不好意思了。
许先生没喝那瓶水。会议结束散场后,我拿了这瓶水,没喝。因为这瓶散发着浓烈的药水气味(后来才知道是来苏的气味)。就在这次会上,我晓得了这清瘦老人是位艺术家。使我惊讶的是,眼前怎么会是画家?初中那些书上写的画家,不是都很有派头的么?以至会议结束回校,王老师坐在大厅的课椅上,发现他穿着运动鞋,心想: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穿运动鞋?还有那头发,怎么这个样子?写硬笔,怎么这个握笔方式?最有意思的是皮带,这个皮带头怎么是巴掌大的银色大象雕塑?望着王老师坐在课桌前写字的姿势,简直就是邻家小孩在认真作业。我不由自主地走近他,问:阿公,你在写什么呀?先生抿着嘴说道:呵呵呵呵,随便写几句做发言稿。从这句话,开始了与恩师15年的交往。
开学后,先生教的是艺术理论。天气渐凉,每天穿着一件很不合身的旧式灰褐色西装,系着一条紫色领带,夹着一条袋,先生说这是乾坤袋,可装很多宝贝,其实里面也就常备三样东西:糖,来苏,尼龙袋的“番钿包”,踱来上课。
那一个学期,讲的全部是他自己学习艺术的经历和心得。每次开讲前,摸出来苏,把讲台擦一遍,边擦边讲:“不要看我这粒布黑,其实干净得很,我就靠它,几十年没感冒过。当然跟我每天洗冷水浴也有关系,我的洗法,与众不同,擦穴道......”






|